位移之外

我还挺直男的,喜欢开车,虽然没开过什么好车。
书里的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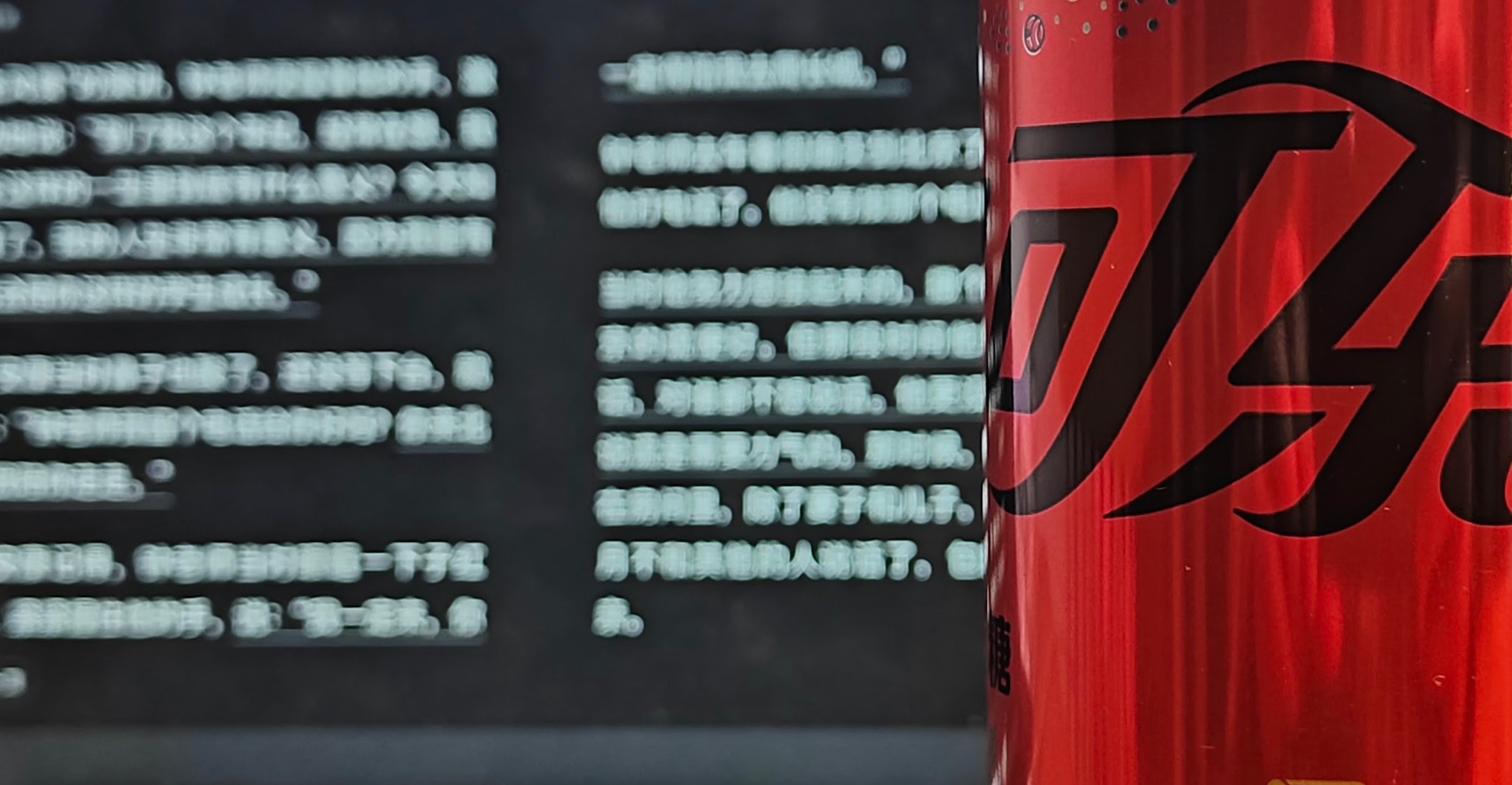
看黑狗达的《草民》,细腻文笔中竟有些韩寒的味道。原来的《皮囊》并不觉得,但《草民》中就非常相似了。而这相似中,有一点相似让我有些许共情:开车。
想想韩寒的1988一书,一般故事都在那个旅行车上;而黑狗达的东石往事,且不说多少情节与韩寒的电影《四海》类似,但就是摩托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就出现过好几次。当然,在电影或小说里,交通工具一直都是重要的情节推动,贾樟柯船、火车几乎已经是时间机器了,而姜文的火车甚至比枪械的杀伤力还大。
只不过,船、火车这样的工具无法自己驾驶,自然少了太多的代入感,不如4个轮或4个轮以内的交通工具能够给人带来更多情绪。
《草民》读完一半,眼睛困乏之际,突然想聊聊自己的朝圣式开车体验,写写记录一下吧。
华北西行入太行

记得初次读三体,罗辑带着人格分裂中的第二人格女友向西漫游,走的就是华北平原的太行山方向。原著中罗辑跟女友是这么说的“今天能见度好,那是太行山,那山的走向会一直与这条公路平行,然后向这面弯过来堵在西方,那时路就会进山,我想我们现在是在……” 答曰“不不,别说在哪儿!一知道在哪儿,世界就变得像一张地图那么小了;不知道在哪儿,感觉世界才广阔呢。”
某个10月,加班重压之下的我只有神游三体的消遣,某个周六下午2点多,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躁动,从北京驱车前往娘子关。走京昆,从北京到石家庄外环,再从石家庄外环向西提升海拔进入太行。
那时候,时值傍晚,还没有进入井陉山区的矿山烂路。疾驰的车辆两边是开阔的华北平原最西端,而眼前是巍巍太行。有那么一会,恍惚感很强,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罗辑的出游,而那时候,我似乎也是在躲避某个生活的短暂出游。
当然,罗辑的车抛锚了,但我没有,我一路到了娘子关发电站。
太行八陉至土木

虽然,我是个历史渣渣,但,对于明史中明英宗北狩到于谦夺门之变的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甚至买了本《明帝国边防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读了读英宗的轨迹,并反复咂摸其中滋味用以下酒,whisky.
某个9月,燥热之中,在读了边防史之后的某日,我开车前往土木镇。即使并不是从故宫或南宫出发,在行至居庸关时,前前后后的旅游大巴簇拥下,已经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气息了。即便我知道,京藏居庸关附近的那些箭楼瓮城什么的应该都是现代工程学之下的杰作,与历史毫无关系,但军都陉这个路线应该依然是历史的行迹。
虽然无法感受到一群动物动力者如何带着一个皇帝旅游的情况,但这种古人多日我们一日的感觉,颇有些欧洲卡车模拟中1km=现实20km的感觉。
一直到土木镇,看到破土墙破土台,终于可以跟自己说一句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啥都看不到。
煤炭味儿的大东北

我算是个西北人吧,《钢的琴》可能是我的东北文化底色的基本构成。
前几天去鞍山,虽然没有某个诸如罗辑或者明英宗这样的具体共情对象,我并不期望一个拐角后满身艳红的秦海璐会出现,但依然不妨碍我把自己对东北的印象与真正的东北进行比照。
或许,可以期待一个路口拐角后出现某个大型工厂生活区;可以期待误入某个巨型工业建筑群。
走入工业博物馆,才得知那样的东北已经在城市改造之下变成了历史。除了博物馆里的地图比对,什么也没剩下。
而,驱车在鞍山街头,依然可以时时刻刻走入钢的琴中,无论是那里的人,还是抬头就可以看到的众多巨型烟囱与连成片的车间。
那种预期与现实对照的满足感,算是另一种朝圣式开车体验。
当然了,如同韩寒的1988所走过的国道,如同黑狗达故事里电死安康父亲的十字路口,每个人总有些压在光鲜之下的以地理位置为标记的刺挠。
就以后再慢慢聊吧。
